
当一个全职妈妈去做导演,她能做成什么样?
这是王一淳曾经面对的问题。在拍摄第一部电影《黑处有什么》之前,她辞去工作,在家作为全职妈妈待了七年,每天的生活就是撸猫、照顾孩子。她不是科班出身,没有电影行业的人脉,也没有短片作品,凭借自己拿出的300万,她开始拍摄一部电影,在片场,工作人员称呼她「姐」,而不是行业惯常的「导儿」。
在人生前30多年,王一淳大多时候都是一个幸运儿:一些天分和努力,再配上一点时代的红利。她发觉,自己总能赶上一个地方的黄金年代,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油田大院、房价不高也不限购时的北京,还有上大学真正能改变命运的那几年。她积累了一些财富,也沉淀了一些野心,总相信努把力,想要的就能达到。
《黑处有什么》后来获得了第九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奖,电影也获得了公映,首映式上,不像其他电影来的都是业内人员——来捧场的都是王一淳的宝妈朋友。
她获得了很多动力,一度觉得自己就要「冉冉升起」了,开始准备第二部作品,这一部,她把目光投诸在保姆身上:这也是她作为全职妈妈时每天要打交道的人群。
她和若干保姆中间发生过很多故事:一些损害,一些误会,她逐渐感受到,在一个相对中产的家庭里,有一个因为幸运成为房子主人的人,也有一个没那么幸运的保姆。而前者的幸运,很多时候可能只是出于偶然。
这些构成了她第二部电影《绑架毛乎乎》的背景。这部电影的钱,还是王一淳出的。对她来说,一直顺利的人生行至这里,似乎有点卡住了。虽然工作人员开始叫她「导儿」了,但转成专业导演的道路还没有完成,「努把力就能行」的逻辑,逐渐不那么管用了。
在王一淳身上,照见了享受到时代红利的一代人曾经的野心,和缓慢的坍缩。但不管怎么样,她觉得,既然电影是个「资金密集型」行业,她就要敲一下试试,「看能不能拿这三百万,在这个壁垒上敲出一个小窟窿来。如果我能爬进去,那很多还在外面的人,也都可能进来。」
以下是王一淳的讲述。
文|李雨凝
编辑|槐杨
1
现在说起来,拍第一部的时候挺不靠谱的,那时候真的是「从零开始」。我一不是科班出身,二没有剧组经验,手里连个短片作品都没有。说别的新人导演,可能会评价「有一些短板」,但到我这儿,没一个长的,目光所及都是短板。当时,我太容易觉得自己做不下去,也指挥不动别人了。
2014年夏天,电影《黑处有什么》在我老家开封的一个油田大院开拍,讲了一个在工厂里长大的小女孩儿,用她的视角去感受工厂黄金时期背后的一些阴影。拍摄周期是30天。在那之前,我已经在家歇了7年,做全职太太,每天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带孩子。
在剧组里,我说是导演,但其实也就刚刚搞清楚了摄影、美术等剧组里各个工种都是干嘛的。现场的职能部门都是花钱组来的。一个外行上来就当导演,还不是因为自掏腰包拍的电影?估计组里很多人都抱着《顽主》里三T公司拿土大款钱财、帮土大款好梦一日游的想法,反正我就从装修小工和小保姆嘴里的「姐」摇身一变成了剧组里的「导演」。
一个整天带孩子、撸猫,日常接触不超过两个人,也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人,突然上来指挥一整个剧组,就像是一个没有武功的人,来给一帮武功高手当头儿,要从各种综合信息判断一个人、一个事儿是不是靠谱,还要谨防被人看透,当别人说到很多专业词汇时,我只能描述这场戏我想要什么感觉,别人的不信服只要没直怼到我脸上,我就当看不见、看不懂,真的用上了从幼儿园开始积攒的智慧和勇气。一个朋友说,你一张口大家就能听出来这人没出来混过。他让我尽量少笑、少说话,这样还能「演」得时间久一点儿。
身边熟悉的人都觉得我是在「玩票」。老公听说我要拍电影,反应是「你都把孩子照顾这么大了,想玩一圈就去玩一圈」,跟奖励一个欧洲十日游差不多。我找到一些影视圈的人看剧本,但要么没反馈,要么给的反馈好像都没看过剧本。一个制片人跟我说他看完了,我很期待地问他意见,他说他的意见是不要拍,新出的某某楼盘可漂亮了,你有这个钱怎么不去买个房?
我不服气,真有那么差吗?后来心一横,真失败了,我认还不行吗?
《黑处有什么》快拍完的时候,我给老公打电话,说,完蛋了,这片子可能拍砸了,拍得不好,钱也花完了,人也都疲了。
电话那边他说,那再加点钱还有救吗?我说,可能不是加一点儿的事。
但挂完电话,我还是要回去,硬着头皮回去继续给大家画饼,鼓励大家一起干活。
剧组是一次性的合作,每天也都是高强度、高资金的消耗。作为一个既往没有任何作品的导演,人家肯定也不指望通过我这一部戏能在行业里树立什么地位。维护这种合作,有一些微妙的平衡,维护这种平衡的能力也是创作能力的一部分。
从喂喂孩子、喂喂猫那种琐碎但简单的全职主妇的生活,一下就来到了剧组这种最复杂的人际关系里,有时候真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一步一坑。很多导演是从剧组最基本的工种干起,一路摸爬滚打到导演这个位置的,什么人什么事都见过,而我就是靠花钱,一下子就当上了总指挥,这么想想,承受点儿质疑和为难也是应该的。哪怕这7年里我多少上个班,也有点职场经验,知道怎么处理人际关系。别人在职场多少年学的那些东西,你就是要放在这些天集中学。我就是这么来哄自己的。
回归家庭,是结了婚,有了孩子后。孩子生出来总要有人来管,我老公那几年正是混得顺的时候,那行吧,我赚不过人家,也认了。就这样,我成了全职主妇。
辞职时,我也想着要留灵活的时间给自己创作,不是奔着「舒服」去的。很多年前我还在工作的时候,一个法国人跟我说,理想的人生就是有三个能体现你人生价值的东西,一间自己设计的房子、一个自己教养的孩子,还有一篇你自己写的小说。我从2002年、2003年左右就开始写这个小说,后来在网上连载,还积累了一批粉丝。后来,我觉得比起小说,影视化的东西能有更丰富的表达,就又开始构思剧本。我之前工作的目标,就是赶紧赚钱,就可以辞职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所以到辞职时,我想,终于要开始我计划的创作生活了。
但回家后挺无奈的。孩子那么小的时候,天天琐事实在太多,吸奶,冻奶,光围绕奶和小孩吃喝这一点就多少杂事。尽管家里有保姆,但也少不了操各种心。孩子还特别容易生病,一生病就一步也离不了人,她有多少成长,我就有多少消耗,纯粹是点燃一个人照亮另一个人的过程。
在早期教育上,我也觉得父母的陪伴和教育是不可替代的,总是不太放心别人带孩子。我也没办法抱怨老公,他也想和孩子亲近,但不知道是不是情商有限,孩子就跟他玩不到一块,还得我上。
总之,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很碎片,就只能在间隙琢磨着剧本,被动安排自己的时间。我只能把带孩子那一部分当成不得不工作的那部分,写作就当成是下班以后的爱好,这样才会平衡一些。
也得承认,平静而又具体的生活会把你往里拖,因为它里面也有快乐,你也会想沉浸其中。那时我真的要时不时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别忘了自己要干嘛,我不能心安理得地花一个下午喝咖啡,我还有正事儿没干呢。
尽管这样,你看我2007年结婚生孩子,真正拍电影已经是2014年的事儿了,整整过去了7年。中间我老公还觉得我整天无所事事,说了好多次让我找个班儿上,别和社会脱节。开始,我还会说我边带孩子边写剧本呢,后来也不说了,自己听着都没底气。
我也知道我是一个没什么自制力的人,确实是浪费了很多时间。再加上带孩子时间过得特别快,一天过去,总是自责什么都没干。所以去拍电影,也算是给了自己一个交待,我是要证明自己也可以做事的。
真正进了剧组,过上那种每天鸡飞狗跳、打仗一样的生活,中间也自我怀疑过,但这么多年了,我总算是开始了,一开始就回不去了。

王一淳在剧组。受访者供图
2
我现在也还时不时感慨,《黑处有什么》有点可惜,但凡当时我有点导演经验,哪怕拍过一个短片,片子都会好很多。但事实就是作为新手,现场永远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拍摄的过程流失了剧本中很多东西。
遗憾还是挺多的,拍摄条件有限不说,有几场我认为挺重要的戏都没拍。所以不仅那几场戏没有,连跟那几场戏相关的戏也剪不进去,最终呈现的和我在剧本阶段的期待太不一样了。当然,拍摄就是在剧本基础上根据实际条件再创作的过程,有加分的部分,也有减分的部分。但我没经历过这个,就觉得,完了,这儿丢一点,那儿丢一点,啥也没剩。
这时候,我只是想着都拍完了,还是要花钱找人剪出来。但我从没看过粗剪片。拿到手一看,都是灰色的,声音也都是呲的,还不如你在婚礼上看的那种vlog,那些都是日常设备拍摄,视频不用调色也能直出。
我直到这时候才知道,为了方便后期上色,电影拍出来的原片都是灰蒙蒙的,连专业名字都叫「灰片」。在没有做任何包装的时候,你看着那个片子,粗剪出来老长的3个半小时,哇塞,全程没调过色,也没调过声音,就是很恐怖。我还鼓起勇气拿给一些朋友看,碰见说好的,我就觉得他们在安慰我;碰见说不好的,我就觉得终于有人说了实话。
那时就想,我认怂了,真得止损了,这事儿就这样吧。
我又回家,继续做家庭主妇。那三百万就变成了一张光盘放在书架上落灰,等于把半成品扔在那里了。我老公那段时间总说,看,我们家最贵的东西就是这张光盘。他还总调侃我,你看人家柴静拍那个《穹顶之下》,不也就花了 100 万?你看人家,你看看人家。
确实理亏,这件事也成了我的一个软肋。我一说老公买了一瓶酒多贵,或者吃了一顿饭多贵,人家直接回一句,这才多少钱呀?还不到 300 万的百分之多少多少。那段时间,只要一提起来三百万,我就不吭声儿了。
最重要的是,我没信心了。我也努力了,我也试了,啥都干了,但好像不行。
后来,一个当老师的朋友告诉我,那一年First影展的李子为在她们学校做宣传,她知道我拍了个电影,问我要不要过来听听,说不定还能报个名。我就去了,到了就问李子为,粗剪片能报名吗?她说能报。我就想,先报上,如果入围了,我就再花点钱调色,做声音。
片子一路入围、提名,每往前走一步我就花一点钱,都是找小的、个人的工作室来弄。全程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反正在家里放着也是放着,人家也没说让你必须现在、马上就做完后期。那我就走一走看一步,万一还能有人看到呢?
那一届影展,我拿了最佳导演奖。一个同学问我,是不是买通了评委?给人多少钱?
我能理解她的感觉,就像是你的一个什么二姨突然拍了一个电影,然后还告诉你,她拿奖了。
到2016年,《黑处有什么》又入围了柏林电影节、伦敦BFI电影节等国内外电影节,通过公映,除了回收当初投入的300万,还挣了个编剧费、导演费,这时我野心又蠢蠢欲动了,没准儿导演这条路真能走。之前我老公不是说 300 万买一个光盘吗?这时他挺高兴,说这 300 万是他花过最值的 300 万。
影片公映时,别人的首映礼都是邀请各种圈内好友,我邀请的就是我从前认识的宝妈们。

《黑处有什么》
3
我有个挺神奇的感受,就是我到哪儿,好像都是那个城市、那个地方的黄金时代。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每一点努力都有所回报。现在看来,这个回报没有那么必然,有一些侥幸,也算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
小时候,我生活在河南的一个石油大院,这种大院行政上独立于所在地区,环境相对封闭,里面谁和谁都认识,跟《漫长的季节》里那个钢厂一样,有自己的学校和医院,也有一个保卫科。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油田在它的黄金时代,里面的人都有一种优越感,外面的人是「地方上的」,言下之意自己是「国家的人」。
我还记得那时候回家的路上总要经过一大片紫色苜蓿,正好我养兔子,它们又特别爱吃苜蓿,现在说起来我还能闻到那个味道。那时候时间过得慢,我就是一个野孩子,在大院旁边的农田偷过麦穗儿,也点野火,烤过葵花籽盘。我妈妈还有一个技校的诗人朋友,我跟着她写诗,加入了学校文学社,诗还发表在油田系统的报纸上。她最后选择去了海南,她的这个选择也被我用在了《黑处有什么》里张雪这个角色身上,那个时候海南刚刚开始开发,是一片承载着很多人希望的热土。
就和《漫长的季节》里王响对王阳的期待一样,院里的职工都希望自家孩子考上中专、职高、技校,然后重新被分回油田,继续安稳舒适的一生。初中毕业时,学习最好的一批都会被掐尖到中专。我中考那一年,油田总部专门出了规定,说全局前200名禁止报中专,必须去上位于总部的高中。很多人都有怨言,还找人托关系,要让孩子上中专。
我也动过上中专的心思,但我妈坚决反对,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她要求我去油田总部上高中。一个朋友,父母也是大学生,她跟我说,一定要出去上高中。就这样,我们俩都离开了油田,离开了大家心目中的铁饭碗。
当时的几个朋友一听我要去上高中,都说你可别瞎考,出了石油系统,将来就分不回油田了。但那时,课本上已经在学国企改革这些东西,很多留在油田的同学后来赶上下岗,也没了铁饭碗,连小时候生活的厂区都被撤了,没油了。
而我到总部上了高中,玩了两年,高三开始收心学习,意外考得还行。这是我最开始感受到「努力就会有结果」。我选了大连外国语学院的法语专业。那是大学扩招前夜,虽然考大学难点儿,但也确实赶上了上大学还能改变命运的年头儿。
1995年,我去大连上大学。当时大连发展得很好,我记得很清楚,入学没几天,碰上基辛格来大连访问,我也跟着人群挤在中山广场,想要跟他握手,最后没握到,反而握到了市领导。
毕业的时候,二炮在招小语种翻译,一去好像直接就是副团级。我妈听了非得让我去报,觉得这是我成为「国家的人」最后的机会。但我觉得,一辈子都要叠方块被子、穿得板板正正的生活,我这种自由散漫的人根本受不了。我就觉得,我是要当作家的人,一想到一辈子要在一个地方上班,过着一眼看到头的生活,我就特别害怕。
因为这样,我到北京找了一个传媒行业的工作。那几年,我为了能有自己作品拼命赚钱,就想着赚够了,就能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我做过娱乐记者,主持过经济访谈,做过户外广告,和城管斗智斗勇。当时确实感觉,每一点努力就会有一点结果,这种事刺激了我的干劲儿,让我也看到自己更大的可能性。
到了结婚前,我赚了一点小钱,我爸去世,给我又留了一点钱。当时北京的房子不限购,首付只要付20%。虽然本地人都说,房价已经涨到了6000块,谁还买?但我们外地人真挺多刚需的。当时又有楼盘在推小户型,我就拿着钱去付了两套首付,其中一套租出去,正好够还两套的月供。
我一路从小矿区出来,到油田总部,又到大连,再安家北京,中间还有一年在国外学习,真的见证了很多的变化和发展。我曾费很大劲想在《黑处有什么》里放一架没造完的飞机,代表一种离开和向外的决心。原本以为所有人都和我一样,看哪儿好就奔哪儿去,哪怕有很多不确定性,要承担举目无亲的风险。但回过头来看,大部分人还是会在一个相对安稳的地方过一辈子。
2014年我回油田拍摄时,我们那个矿区还在,走在街上,好几个老同学认出来我。我就奇怪,这些年我老了这么多,他们怎么还能认出来我?
但我一开始都没有认出来他们。在我看来,这些同学的相貌已经变得跟我记忆中的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而他们好像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一个曾经和我挺有交情的女同学连连惊叹,你竟然认不出来我?你怎么会认不出来我?最后她说,就是你这些年见过的人太多了,眼迷了。
这件事让我还挺有感慨的。经历不同,一个人笃定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眼里可以完全不一样。
人到中年,终于过上了理想中的靠文艺过日子的生活,有时会觉得得益于自己的坚持,但其实幸运的成分更多。
前段时间我堂弟来北京找工作,正好我一个演员朋友在录一个试戏视频,就让他在旁边搭戏,没想到他搭得那么好,不仅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还能根据演员朋友表演的变化顺势调整。这个堂弟年轻时很帅,也喜欢电影,我上次见他是十几年前,他一直在聊巴西电影《上帝之城》。这次见他,一直在聊他酿的酒,跑的工程,我想让他和演员朋友一起去那个剧组,他担心耽误业务,就没去。我挺替他惋惜的,但他好像也没太惋惜。
我后来明白了,其实有我这种愿望的人,可能比看起来要多得多,但很多人都淹没在具体的生活里,都被很具体的生活压倒了。

图源剧集《漫长的季节》
4
有孩子这些年,最深度接触的是各种各样的保姆。上面说的这些感受,也和她们有关。
有一个保姆,在大扫除时,把我们家人的电脑放在了外面垃圾桶附近的草坪上,找到的时候,电脑上面还盖了一层薄土。虽然监控没有拍到,但那一个上午,只有她去过垃圾桶附近。
还有一个保姆来北京陪孩子读大学,自己也是大专毕业,自尊心很强,听见我用外语接个电话,就会说「我大伯家的孩子会五门语言」。她说话爱用一些文学化的词,类似于「我当时很惘然」。
还有一个是小时工,我刚搬完家,要清理出去很多东西,她帮我收拾,我发现找不到手机了,让她帮我打个电话,结果,铃声从她的工具包传来,手机在她工具包里的底部找到了,她是在我家工作了很久的小时工,我们一直处得很好,所以我们都没多想。但那天她走后,我装电脑和iPad的包也不见了,我报了警,第一怀疑对象也是她。两天后,楼长告诉我,那个包在物业,是楼道的垃圾清理工在我家清理出去的垃圾里发现的。是我误会她了。
我想起来,这个阿姨跟我讲过,她是从四川嫁来北京周边的村子的,老公家暴她,每天就躺在家里靠她来养活。她身上很多淤青。她还跟我讲过之前就曾经被雇主冤枉过。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和警察冤枉她时她的反应,非常平静,事后对我也没有任何责怪,还总是问我家里是否需要帮忙,反倒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关系。
这也是我第二部长片《绑架毛乎乎》的灵感来源。所谓一个人生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命题,这就是我结婚生孩子这7年里最熟悉的日常生活。在影片中,在一个相对中产的家庭里,有一个因为幸运成为房子主人的人,也有一个没那么幸运但并不认命的保姆。
回望自己走过的路,每一次努力都有所回报,这其实很容易让人虚妄。一路走到罗马的人甚至比那些出生在罗马的人更虚妄,觉得自己又聪明又能干,懂得把握人生的每一个节点和契机,但实际上,同样天资的人很多,生活中一点小小的误会就足以让人错过自己最想过的人生。
选择保姆作为第二部电影的题材,也是因为我目前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家有保姆的中年中产家庭。所谓中产其实挺脆弱的,这两年经济不好,会很直观地反映在周围人的变化上。
想一想很有意思,没有任何一个职业像保姆一样,把教育、职业、收入、观念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甚至两个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保姆到一个家庭里通常是来照顾孩子的,孩子又通常是一个家庭的核心,牵动着全家几代人的心,而最多照顾孩子的保姆其实是一个「外人」,这个「外人」也有着自己具体的情感、过往和生活,虽然在大多数时候,她的情感、过往、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是隐形的,不重要的,但却每时每刻都具体、逼真、不容忽视地存在着。我自认为一路走来对从小镇到城市各个人群的生活、境遇都有所了解,有所体会,写这样一个故事让我这些认识、体会有一个变现的机会。
在《绑架毛乎乎》里,保姆和男友一起绑架了主人家的小孩,并说好了只要钱,不伤人,但后面的一系列事件逐渐脱离了她的控制。剧本在2018年拿到了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具价值投资项目,后来,又被我带着去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也是当年中国唯一的入选项目。
电影是一门「资金密集型」艺术,创作成本为它筑起了一道天然的壁垒。说起来是大众艺术,但大众能参与的只是看,或不看。完全能想象,像我一样想尝试参与制作的人还有很多,可能有的人也真的很不错,肯定还是有一些剧本,就躺在抽屉里。可能很多人都想拍,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出那三百万。我就是幸运有这笔钱。
既然是个「资金密集型」行业,那我有了这三百万的敲门砖,能把我垫进去吗?我就敲一下试试,看能不能拿这三百万,在这个壁垒上敲出一个小窟窿来。我很幸运,花钱买了张门票,让我有机会到这个壁垒森严的产业里转一圈看看,像逛了个环球影城。

《绑架毛乎乎》的主角,保姆石俊霞 图源豆瓣
5
拍《黑处有什么》的时候,我想,这部弄完就别弄了,证明自己能做就行了。但得到认可后好了伤疤忘了疼,想着苦应该也差不多吃完了,就跟吃甘蔗一样,把难啃的啃掉,是不是接下来就应该甜了?身边的人也都说,王一淳成了,接下来肯定要拍大片了。
在我以为前路光明的时候,2020年来了,影视寒冬了,我就真的体会到了不是偶然的「不幸运」。
但那时候,我的第二部电影《绑架毛乎乎》已经进入筹备期,演员都谈得差不多了,我和投资方因为撤资打了一架,人家还胜诉了。我又变成了自费拍片,这次比上次花的钱多多了,后续一切宣发也靠自己张罗,各种事连门都摸不着,完全不知道钱能不能收回来。前几天我还掉眼泪,老公这次倒没怼我,可能怕我跳楼,还安慰我,说可以了,挺好的,没事儿。
第二次拍电影,也遇到了很多幺蛾子。带着疑惑,我甚至去一些大导的组里观摩,结果发现幺蛾子也不少,但好在人家有钱填补。我本来以为自己最烦写剧本,经历了拍电影过程中的各种人和事,才发现,写剧本是整个过程中最纯粹快乐的部分。
这也是我这些年都在琢磨的:在一件事上,为了自己感兴趣的1%,要做99%不感兴趣、不擅长甚至厌烦的事,值吗?很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使把劲儿,说不定就能够着」的心态,以前那么多不敢想的事,后来都成了,包括拍电影。但现在,我确实有一点儿摸到了人生的边儿的感觉,没准儿就这样了,心累了。最初想留下个作品的愿望也实现了,能证明「这个事儿我会干」就行了。
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我还怀孕的时候,别人的祝福都是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得长得像妈妈,智商像爸爸。
我就想,智商怎么就不能像我?人家也是好心说这个话的,但他们就默认你是家庭里没脑子的那一个。
现在没有人这么说了。现在别人至少会说,哎哟,这孩子的艺术天分是遗传了妈妈。我听着就很高兴,好歹忙活一圈儿,也算显示了一点基因优势。
当然,如果能不那么累就能维持这个「导儿」,我就还想维持。如果不能维持,那就只能回去当「姐」了。不管怎么说,这么来一趟,我知道继续走下去,自己也能成为「somebody」了。


王一淳和剧组里的孩子受访者供图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CYQY-生活与科技 » 一个全职妈妈掏出300万,做导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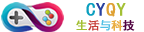 CYQY-生活与科技
CYQY-生活与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