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飞:上期我们说到当前行业形势分析与传统编剧生存之道,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行业就像我刚才讲的,我最开始讲的责编、文学策划那方面的大师是怎么做的?现在是什么问题呢?现在是所有的责编,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责编,当然不排除有个别老编剧、老同志都改行来当责编,或者当责编的领导,这有可能。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有些人比如他没有写过剧本,甚至他大学刚毕业就来做这个责编的工作,他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写了十年八年的老编剧。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交流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这个年轻的责编并不懂剧本创作的方方面面,他刚上班,可能就是他们公司给他培训过几天,说了一些情况。因为平台要接受的剧本容量很大,所以不得不去让这么一个人管几部戏,说不定管几十部戏都有可能。这个人可能从来没有创作过,也没有接触过编剧,但是对他讲,这只是他大学毕业拿工资的一个工作。
谭飞:江湖谣传——月工资8000的责编要管一集戏几十万的编剧。
余飞:对,那么这个情况的复杂性在哪儿呢?这个人他必须要干这个事,因为他拿了工资要干这个工作,必须要干,不管懂不懂,他也必须得干。但是对面可能是一个从业十年二十年的老编剧,他很懂这个行业,而且他今年能不能买房子或能不能送孩子上大学就靠这个戏了,他寄予了全部的希望,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在这种对接的情况下,大家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判断力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对等的,是不太科学的。但问题是平台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别厉害的责编,因为没有一个专门培养责编的平台。

谭飞:因为太难了,好的责编应该是一个人精,各方面都很厉害。
余飞:又会办事,又懂剧本,而且最好还有权力,因为你没有权力,你跟我说也解决不了。
谭飞:还得有地位,资深还得在这儿。
余飞:对,所以现在责编的尴尬处境是什么呢?他并没有真正的话语权,他弄完这个,还得报领导去。
谭飞:像个二道贩子。
余飞:他还得报领导去,所以他没有权,他也不能直接说我答应给你钱,而且他提的这个意见,有时候这个意见并不是直接真正能作用在这个剧本上的,而且他的编剧经验,还不一定有这个编剧的经验强。这个编剧之所以听他的,不是因为他说得对,很多时候只因为他在这儿。
谭飞:他这个职务。
余飞:他在这儿,就像你进小区有个保安,他就不让你进去。
谭飞:他相当于平台方代表,你得听他的。
余飞:他是平台方的领导或者说领导层权力的一个化身、一个代言人、一个替身、一个执行者、反馈者,这完全没有任何错,完全是对的。问题就是现在主流就这四个平台,但是全国可能几万家公司,咱们不说几万家,肯定有好多破产的不算,哪怕就五千家公司,每个公司如果一年只做两个项目,一个项目肯定不可能,一年做两个项目,那也是一万个项目。一万个项目来找我们这些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谁干得过来?即使有经验都干不过来,如果没经验的,那完全就是懵的。所以各种人挖空心思要来接近这些人,来想办法让他通过。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呢?甚至有可能导致权力寻租,我给你点回扣,我送点啥东西,我给你干个啥事,你帮我通过一下,走关系什么的,那就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这是极个别现象,但是很可能会有。
二
中生代编剧面临的困境有哪些?
谭飞:我给大家念一下余飞老师振聋发聩的这段话:
“IP体系取代编剧原创体系,平台赢利困难并且自制成为大趋势,制片行业艰难,编剧行业协会沉默,限价以及法务方面大量严苛条款、平台和制片公司无力培养大量高水平文学策划导致只有头部人员才能走绿色通道等等大家都发现但又没办法的问题,导致编剧行业唯有头部和新手(无知无畏或入行就习惯这种场景)有劲头干下去,中间层生存极其艰难,有可能会被完全边缘化,最终导致整个编剧行业创作力量断档(IP产业是不提供专业编剧的,一般情况下,作家改行的编剧能力不可能马上就达到专业编剧的水平),这个巨大的危机才是值得谈的。”
谭飞:中间层生存极其艰难。甚至很多人可能就吃不起饭,有可能被完全边缘化,于是纷纷改行,最终导致整个编剧行业创作力量断档,这是个巨大的危机。
余飞:确实有改行的。是这样的,因为作为平台它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虽然说有新生代的编剧,但是这帮老编剧全国不一定很多,大几百人吧,其实是我们这几十年创作留存下来的最宝贵的人才资源。但这个资源现在正在被边缘化,甚至已经被边缘化了,只有数得着的可能十个二十个,比如说我可能是其中一个,这是大家能看见的,而且平台比较重视的,项目运作还相对比较容易的,比如像赵冬苓老师。
谭飞:高满堂老师、刘和平老师等等。
余飞:对,但这样的人已经不是太多了,就这么些人还可以。然后新生编剧刚入行,反正他啥也不明白,他觉得刚出来就这样,他就认为是这样了。
谭飞:而且他的成本相对也低。
余飞:他无所谓。
谭飞:他遇到挫折就遇到吧。
余飞:他不行他改行也来得及,他属于这种情况。
谭飞:因为他年轻嘛。

余飞:但是中间这一层,比如说有五百个人,这五百个人都是有过播出作品,甚至有的还获过奖什么这些,这样中间层的编剧,这些人可能都是四十到六十岁之间,应该是大概这么一个年龄层,正是创作最成熟、最黄金的时期。但这些人现在被边缘化,不知道都在干啥。即使有人还在这个行业里干着呢,很多人也都是非常艰难。因为说白了,最简单的一个事就是跟他对接的这个人,其实是没有能力来指引他、也没有能力来给他承诺的。但是这个编剧还不得不配合,进行无休止的折腾,让你改十遍,改一百遍,你都得弄,不对也得听,还不能反驳。而且他们也没有能力找到他上面的人去帮他说什么,而且这样的人往往做的项目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项目。因为以他的资源,或者以他的所谓的名气,人家认为他没有那么大价值,所以更高的投资,比如说投资两个亿三个亿,甚至四个亿五个亿的项目,也不可能找他,可能就投资个五、六千万的一个项目找他,那这样编剧的费用、各种配置都会下降很多。这种情况下,平台对接的人肯定不可能用最好的资源去对接,因为人家有那么有名的大的项目要做,那他哪有精力来管理这么小的项目呀?你这个管好了也没有多大含金量,对他来讲,也没什么业绩。
谭飞:他们等于是在大量的无效劳动,又只有非常微薄的酬劳,而且也不能保证未来的这种情况。
余飞:这里面就很自然地又涉及到各种什么权力寻租也好,或者是这种被“霸凌”也好,还是什么,虽然各种情况,不是故意的,首先我说。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来从事这个工作,是他的工作,他必须得干。
谭飞:对,得对得起他的工资。
余飞:我不懂我也得干了,要是我,我也明白。
谭飞:不懂得硬着头皮干。
余飞:我不懂,我硬着头皮,我学习,我可以干的过程中学习。但我学习的成本很低,而且我也不会失去什么。但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把这个老头整“死”了。
谭飞:一个月薪8000的人轻易就决定了一个男人的生死。
余飞:因为那个人毫无还手之力,他还不了手,因为他不认识别人。哪怕过去认识电视台一个主任还能问两句话,但现在没有用了。
谭飞:听着也挺悲催,但是好像这个一下也改变不了。
余飞:是的,平台肯定也想改变这个状态,但是没有那么多人才。而且这个人如果专业能力极强的话,他也不愿意干这个职业。
谭飞:他有可能就自己去写了。
余飞:对,我写这么好,我为什么要去替别人看剧本?
谭飞:因为你肯定是比大编剧的酬劳低得多的。
三
如何应对编剧行业创作力量断档危机?
余飞:所以我认为首先一个就是说,还是要重金来聘请好的责编和文学策划。我曾经就在优酷办过一个大师班,我们去讲课。我讲完课以后,我就当天下午和晚上分别给两个剧组辅导他们的创作。现在我的身份就是策划或者责编的身份,其实相当于就是给优酷当这个身份。聊得非常好,我也没看出编剧有任何不服气的地方,都特别高兴。编剧、导演都在,制片都在,聊得特别愉快、特别高兴。有些老同志他写不动了,他的精力有些写不动,但他看是可以的。
谭飞:相当于高级顾问嘛。
余飞:对,其实这个我认为是可以的,而且这样的人一个人他带那么四五个人培养,他是有可能培养出来的。
谭飞:师傅培养徒弟。
余飞:对,但前提是他要在这儿能说了算,他就带那么四五个人一个小组,专门看剧本什么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应该是朝这个方向努力。要不你全靠责编新手来进来,就进行一些最基础的业务培训以后就上岗,这个不是,因为编剧创作是太复杂了这个工作。
谭飞:我理解余老师说的。可能这种倒挂,或者说这种畸形,或者不匹配,非常非常的突出,而且非常明显,但是好像一下子也改不了,就一直持续。
余飞:就好像说我们希望在五年之内再培养十个获诺贝尔奖的作者,那是不可能的。不光是说你拿不出待遇、精力的问题,还有天赋问题呢。
谭飞:余老师您刚才说四十岁到六十岁的很多中年编剧的这种状况,你的目光所及,你的周围看到这些人他们现在是什么状况,是不是很多人转型?我听说有开滴滴的,还有转行做什么的?他们现在的一个出路在哪呢?
余飞:有些写短剧的,有回老家的,有原来在北京现在搬到外省去的。
谭飞:房租都给不了了。
余飞:对,这些我身边都有,最近这两三年,我知道的、认识的已经有去世四位的了。
谭飞:是什么原因呢?
余飞:有跳楼的,我在微博上都悼念过这些,那个跳楼的黄老师,我还请他吃过一顿很贵的铁板烧,本来还打算跟他合作的。听别人说他还在背后说过我很多好话,说要感谢我什么的,但是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他去世一年了。我其实很想帮,但我没有那么强的能力,而且在那个时期我也处于一个左右观望,该怎么办,也有这种彷徨的时候。因为有很多都是我的好朋友。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况,经过从大IP爆发到平台转型以来这么长的时间,有些人其实很长时间都没有练手了,没有练手就越来越不行了。本来如果情况都挺好的,他可能还能发挥他的强项,但你那么长时间不练手,没有实战项目给你用的话,即使在过去还可以的,但你现在弄都不一定行了,但你心里那股自尊心还在,自己对自我的认知还在。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特别屈辱,而且年纪又大了,被人家小孩劈头盖脸地一顿提意见。
谭飞:呼来喝去的。
余飞:他会很难受的。所以有时候我看着,我可能很侥幸,一直坚持我这个赛道在弄,弄得还可以。但看到好多这样的人,我心里也很难受,也有人说你混得挺好,你怎么不帮帮他们?那我一个人,我说怎么帮?帮谁?我自己也都没看太清楚呢。我是这种感觉,就好像我自己在山顶上建了一栋房子,我的家乡父老都在山脚下,但现在发生泥石流冲倒了他们的房子,我没法救他们了,我咋救?这是一个大的自然界的一个趋势。
谭飞:大的洪流。
余飞:我救不了,我只能看着心疼难受,事后去安慰一下。
谭飞:但其实余老师揭示的这个真相很重要,可能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我们一方面呼唤好的作品,同时另一方面对我们作品的创作者,我们要更多地用专业的角度去帮助他们、引领他们。不管是现在这个结构性问题,还是系统性问题也好,总得想一个办法。
余飞:现在很现实,现在这个情况是不可能全都挽救的。现在只能说发掘出一些能力很强但是暂时被埋没的同行,我们稍作启发,给一点机会可能他们又能重新绽放出光芒。最好把他们挖掘出来,把他们救出来。如果本身过去的水平就处于不是很稳定的状态,又这么久没有工作的人,我们可能就真的很难救过来了。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这一两年我心情很不好?虽然说播出了一些作品,又获得了一些奖项,但情绪一直有些低落。这感觉就像我跟我们编剧的同行都在一个火车站台上等着车,我们要去往很美好的一个前方,结果突然看到好几列火车全都出轨了,直接奔着站台呼啸着从我身边冲过去,把我们的人压得七零八落,我只是站在中间侥幸没被撞着。但等我缓过来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同行倒下了一大片,再抬头看见火车跑一段后又正常开走了,那我现在还能追,能搭上最后一班车,有好多人就根本跟不上了。
谭飞:所以我理解你的难受在于说,你觉得这个行业在现在这种冲击下,特别是如果有些东西没做好的话,可能很多人才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他的劳动和付出完全得不到回报和成正比的一个收获,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余飞:对,那是多少年培养出来的人才,因为我们行业没有好好地总结和归纳,这个很可惜。我1997年入行,到现在快30年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经验,无论是剧本创作方面,还是剧本的运作、管理方面,哪怕当责编、当策划,都有很多很多经验。我们其实应该是大家都共同联合起来,把这些经验都贡献出来,完全可以编出一部《辞海》来。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合起来编撰,也不告诉别人我们有编这个《辞海》的打算。所以人家平台自己编了一个《新华字典》现在也能用,人家现在这个用得挺溜了,你这个《辞海》迟迟不编出来,慢慢地人家不用了,把《新华字典》不断地丰富,最后变成一个自己的《辞海》,对不对?

谭飞:对,或者这么说,就是一个略显清高的行业,当时代的列车跑得很快,他们自己也造了一帮人一起跑的时候,这边想追上他们。第一,发现他们前面都是年轻人,第二,发现其实有些跑得快的慢慢也跑不快了,是因为没有人来给他们一个饮水的地方,一个发什么饮料的点。
余飞: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平台现在也不是说过得特别好,特别舒服。
谭飞:都是好不容易才盈利。
余飞:平台也有巨大的危机感,包括AIGC这些发展,他们有巨大的危机感,所以你让他回过头,转不回来。
谭飞:它根本顾不过来。
余飞:顾不过来,你有本事你追上。就像非洲大草原里面,一头小象落伍了,你追不上,就有可能被别人吃了。
谭飞:就是自然界法则物竞天择。
四
余飞对编剧行业的三点建议
余飞: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呢?我们编剧也要主动地跟上,但是平台和主管部门也要多做一些交流的可能性,给大家一些交流空间,或者把合同,把这些东西做得更规范,让大家都有一个发展的可能,这样我觉得才是一个好的现象。

谭飞:余老师说了三点建议,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些老师傅们、老编剧们,你们可以在退休后,或者说你实在不想写了或者写不下去之后,你当一个师父,培养徒弟,这些也是一个培养好责编的路径,甚至自己当总顾问,来做一些文学策划方面的事儿。第二个就是平台也多跟编剧交流,主管部门也多交流。第三就是在合同、合约的制定上,能不能做得更科学。
余飞:最近一段时间,我明显地感觉到有些合同上表达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包括最近我又发现,有很多甲方就完全连发表权都不给编剧。因为发表权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权利。
谭飞:天然的权利。
余飞:我写完东西不发表的吗?它是人身权,它不是财产权,它是天生就应该有的。但连这个东西都开始出现争议了,好像说惯例是不给这个发表权,这样对作家来讲还好,因为作家肯定要发表他的小说嘛。对编剧来讲,或者说对于剧作家来讲,这就要了命了,因为剧本就不能发表。这涉及什么问题呢?一旦这个项目出问题,这个剧本就永不能见天日了。而且万一出现侵权事件,你没有发表权,你都没法拿这个剧本出来给人比对,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权利。
谭飞:有理了都没法说。
余飞:对,最基本的一个权利都丧失了,这就非常吓人,更不用说有很多别的条款。
谭飞: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对,还是得几方坐下来,因为可能有些细节或者有些专业有壁垒的东西,别人也不一定知道怎么回事儿,几方得坐下来。
余飞:确实是形势比较严峻。

谭飞:我看得出余老师的焦虑,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想让更多的观众和读者知道咱们现在编剧界的一个现状,大家也能帮着出点主意,想想办法,提供人才或者提供一些思路,也都是好的。
余飞:因为现在确确实实是从平台到制片方,到编剧,还有中间其他导演、演员,各方面都不容易,过去还说谁抨击谁,谁批评谁,现在是谁也别说谁了,大家都不容易,都在这个行业,尤其还有国际上的竞争,因为现在网络一上去都能看见,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拍不出好作品来,就都去看国外的了。
谭飞:就相当于说在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谁还会关心最弱的那个人的生死呢,是吧?
余飞:对,但编剧是个什么行业呢?他的发声和行动能力是比较弱的,尤其是没有实权,但是这个行业确实是以他为基础的,就是说你哪怕看到他再讨厌他,但确实没有他不行。而且他很重要,他弄出来这个东西很重要,你不重视编剧那无所谓,但剧本确实很重要,没有剧本你别的都免谈。所以无论说对编剧有什么成见,对编剧行业有什么成见,但是为了咱们这个影视行业或者说视频行业,甚至游戏产业都跟这是相关的,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相当于某种意义上的宣发部门,我们这个宣传部门是要海外去竞争的。中国故事要讲好,首先是编剧的作用要起到。虽然说他很弱势,他没有实权,但是必须要重视这个事。

谭飞:还是得尊重和重视。
余飞:所以一定要搞一个比较良性的机制,来让编剧去为它拼命,我们愿意拼命,但是别为不值得的事拼命,那没必要。一定要把这个机制建立好了,我们愿意付出最大的热情。
谭飞:就是让真正有才华的编剧在一些靠谱的项目中展现他的才华,而不是说让他长期处于一些不靠谱的事儿的一种纠缠中。
余飞:又没有希望,又没有钱。
谭飞:又费马达又费电,还费身体。
余飞:甚至署名也没有,天天生气,这确实是没有必要。
谭飞:好,谢谢余老师今天的肺腑之言。
余飞:谢谢。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CYQY-生活与科技 » 余飞:新责编与老编剧错位现状及未来行业融合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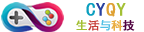 CYQY-生活与科技
CYQY-生活与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