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金马影展|北野武导演金马电影大师课
北野武,导演、编剧、演员。从大学辍学逃家,于脱衣舞剧院当电梯小弟兼喜剧学徒,其后以肆无忌惮的双人漫才成为家喻户晓的综艺谐星与主持人。1983年以大岛渚执导的《俘虏》跃上大银幕,1989年初执导演筒的《凶暴的男人》即荣登电影旬报年度十大影片,再以《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勇夺蓝丝带奖最佳影片及导演,戏谑更显讽刺,残忍更见温柔,于极致反差中将人性宿命赤裸呈现。曾三度入选戛纳影展,六度入选威尼斯主竞赛,以《花火》、《盲剑侠》夺得金狮奖、银狮奖最佳导演,是日本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殿堂级导演,更是集画家、作家、诗人、评论家于一身的传奇人物。
时间:2023年11月23日(四)16:40 - 18:00
地点:台北文创大楼14楼文创会所
讲者:北野武KITANO Takeshi
主持与谈:侯季然
口译审稿:张克柔
文字记录:林子翔
摄影:蔡耀征
文字授权转载自「金马影展」
侯季然:大家好,很荣幸今天来担任主持与谈人。其实今天的问题都已经翻译好给北野武导演了,但是刚刚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问他什么他就答什么,每次回答的内容都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的任务就是希望他可以放飞自我,讲越多越好,相信他会讲出很精采的内容。那我们欢迎北野武导演。
北野武:首先非常谢谢金马影展邀请我来担任大师课的讲师,因为我在日本影坛是个被讨厌的问题人物,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分享一些对大家有用的知识,但是很荣幸能够受邀。
四格漫画的起承转合漫才带给电影的精准节奏
侯季然:今天的提问会以电影的创作跟制作为主。第一个问题想请问导演,你在题材的选择上面,有非常个人的作品,例如《菊次郎的夏天》、《坏孩子的天空》等,也有改编历史故事《首》,让你想要拍一部电影的念头是从哪里来?怎么选择题材?
北野武:当我觉得某一个想法,能够发展成像报纸上面的四格漫画一样,有起承转合的结构,我就觉得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了。灵感的来源有很多,譬如看到一则很有故事性、很适合发展的新闻事件,我就会把它写成剧本大纲,再看看有没有发展的机会。不过大部分还是像刚刚说的四格漫画理论。

北野武《坏孩子的天空》 (1996)
侯季然:导演也会自己写剧本,在写剧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写一个剧本需要花多久时间?
北野武:我觉得编剧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四格漫画,要有起承转合,所以我在思考故事时,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架构,然后在脑中浮现比较重要的场景或类似分镜的画面,接着再慢慢针对这个故事的想法、桥段、情节等增添血肉。不管是在录制电视节目还是在跟朋友出游的时候,都会把笔记本带在身边,想到什么就写上去,渐渐地让故事成形。如果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就会有剧本的雏形出来。接下来我就会召开剧本会议,找工作人员讨论。跟工作人员说明的过程也有助于我厘清思绪,再重新梳理一遍故事的架构。然后在剧本写到大家都觉得够好之前,我们会开多次剧本会议。但是每次开会我讲的内容都不太一样,工作人员都有点吃不消。(全场笑)

照片来源:金马影展
侯季然:导演从第一部作品开始风格就非常鲜明,常常在浓烈的戏剧当中,突然有中断或疏离的时刻,甚至有时候会在观众很入戏时插入幽默的情节。请问导演对作品的情境或叙事节奏,例如招牌的疏离跟幽默、定镜、忽然的无声等,都是怎么样设想出来的?
北野武:我认为导演就是观众的代表,所以我会做为作品的第一个观众来检视自己,有些戏会不会太残酷,会不会看不下去,然后尽量发挥,拍到不超过自己底线的极限。当然我在拍戏的时候,也会考虑很多客观的因素,譬如拍摄预算、当下的身心状态或是在日本演艺圈的地位等,这些也会影响到作品风格。但是我认为最好的方向,还是身为观众有没有办法享受这部作品。

Two beat时期的北野武
侯季然:北野武导演在第一次担任导演之前,就是很成功的主持人跟演员,这些经验对导演这个角色来说有没有什么帮助或化学作用?
北野武:电影是一门综合的艺术,涵盖了多元的层面,不管是音乐、视觉、文字或演员的表演等,当然搞笑、幽默的元素也包含在内。不管是以前在小剧场表演的搞笑漫才,或是在电视上的唱歌主持,全都涵盖在电影需要的综合艺术当中,所以这些经历对我拍电影都相当有帮助。不过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当我刚开始拍片的时候,明明是黑道片,在很严肃的枪杀场面,因为我有搞笑艺人的身分,所以观众看了会笑。但是我现在比较少在电视上搞笑了,所以大家现在看电影比较不会在非预期之处笑出来。

北野武《花火》HANA-BI (1997)
侯季然:接下来我想追问一下,北野武导演在拍电影之前也是很成功的漫才师,漫才是很独特的艺术,导演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请问表演漫才的经历,对拍电影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艺术性有没有共通的地方?
北野武:漫才是日本的双口相声,在美国也有一些歌舞秀的中场表演,会出现类似日本漫才的形式,但是大多是像艾迪·墨菲(Eddie Murphy)那样的单口相声,双人的组合比较少一点。不过在日本,双口相声,也就是两个人组合的漫才,工作机会比较多,所以大部分的谐星会选择双人的形式。我觉得漫才跟电影的共通点,就是很讲究节奏,日文称为「间」(ma)。
漫才的经验让我对抓节奏变得比较敏锐。以前用胶卷拍片的时候,一秒是二十四格,我们在剪接时会凭感觉修剪十格、十五格,这都是在一秒之内非常细微的调整。漫才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搞笑时如果节奏稍微跑掉了,观众就会笑不出来;节奏在那个点上面,观众就会哄堂大笑。所以我觉得表演漫才的经验,让我在无意识之间在拍电影上,对节奏的掌握更加精准。

北野武早年参加漫才节
相信直觉的选角哲学表演只有一次机会
侯季然:导演曾经在访谈中提到,你不试镜演员,也没有排练,请问导演是怎么挑选演员的?什么样的演员会让你有兴趣想要合作?怎么看待演员在电影当中的角色?
北野武:选角的时候,我最重视的是直觉。直觉会告诉我,可以让这个人演演看这个角色。其实这部分跟男女关系蛮像的,当你遇到一个对的人,你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如同这种男女关系的本能,有时候即使还没有沟通或相处过,光是看第一眼就知道是喜欢还是讨厌这个人。我蛮相信自己在这方面的直觉,不过相信归相信,我也失败过很多次就是了。

北野武、大岛渚、坂本龙一
侯季然:接续演员这个话题,在拍摄现场,如果演员演出来的感觉跟你想像中的不一样,你会怎么沟通?如果在现场发现演员完全不适合,该怎么办?怎么让演员进入状态?
北野武:我自己是漫才师出身,同样的搞笑不可能重复两三次,在剧场就是要把每场的客人都当作是第一次看这个表演,我也是第一次表演这个段子。对我来说,电影虽然会在事前先给剧本,但是表演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所以我拍电影的时候,基本上只拍一次,也没有排练,直接正式来。当然我也会有没拍好、需要拍第二次的时候,如果重拍的原因是演员的表演不如预期,那第二次我就会把摄影机转过去一点,拍他的背面或后脑勺,尽量避开演员的表情。万一第二次又失败的话,我会把摄影机的位置改到侧面,假装拍一拍,但是我没有要用这颗镜头。(全场笑)

高畑秀太《红鳉鱼》 (2015)
侯季然:导演起用的演员类型很多元,像刚刚播映的《首》,很多大牌、知名的演员,但过去的作品也有像《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起用新人、素人演员,也有用过小孩子。导演在面对不同质地、经验的演员们,会用什么不一样的方式引导他们?
北野武:不管是用无名、有名的演员都各有好坏。比如用素人演员的时候,有些人会因为没经验而求好心切,事先熟读剧本、费心做足准备,但他表现的东西不一定是我要的。这时我会换一种沟通方式,引导对方做出我想要的感觉。譬如有一场戏,是一位素人演员饰演杀手,到一个废弃的空屋寻找仇人,但是他演得太用力了,看起来很刻意,所以我在现场就骗他说换角色了,你现在不是演杀手,你是一个在寻找今晚过夜地点的钓客,看到这间空屋就进来确认一下屋内的状况。后来他按照我的指示去演,感觉就对了,但实际上他在戏里的角色还是杀手,我只是换个说法让他不要刻意去表演。
再举一个跟小孩合作的例子,我当时给他们一些零用钱,跟他们说现在去帮我买冰淇淋,然后就拍他们跑远的身影,这也是跟剧情无直接关连的指令。如果跟比较有经验的演员合作,譬如刚刚播放的《首》,里面都是很有名气的演员,有一些他们要死掉的戏但一直不死,该死的时候还在继续演,曾经逼得我大骂「快死啦!」;不然就是好不容易要死了,演员居然给我往前走,刻意倒在镜头前面,又搞得我很火大。所以经验值也是有好有坏,真的什么状况都有。

北野武《菊次郎的夏天》 (1999)
导演与剧组成员的关系掌握暴力的底线
侯季然:导演现在累积了很多电影作品,有像是《首》这样的大制作,也有跟北野组常合作的剧组跟演员。回到第一部长片《凶暴的男人》,这部片本来的导演是深作欣二,后来决定由你来接手,那第一次当导演到现场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剧组人员合作?有没有跟现在不一样的技巧?
北野武:《凶暴的男人》是我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它原本的导演是深作欣二,他在日本以擅长动作片闻名。当时深作导演想找我当男主角,一开始合作谈得很顺利,但是我那时电视台的工作很多,一个月只能分出十五天去拍戏。深作导演听了之后蛮生气的,他说「你不能每天都来的话,我就不拍了」,因此后来深作导演就辞掉了导演职位。当时出品的松竹电影公司跟我提议,有没有兴趣自导自演,所以我就成为这部片的导演了。
原本预计跟深作导演的剧组,直接转来陪我拍这部片。可是那时业界有一些负面传闻,说我一个电视艺人跑来拍电影不成体统,也听到有人说绝对不会帮忙我。所以我在开镜那一天,头上戴了那种上面剃光只剩一把头发的武士假发,手拿日本刀,身穿和尚袈裟,脸上戴着剑道的面具,用奇装异服出现在片场。剧组所有人都吓到露出惊恐的表情,觉得这个导演脑筋好像不太正常,如果不帮他的话这部电影会完蛋,因此剧组变得很团结,我也顺便拍完了这部片。(全场笑)

北野武《凶暴的男人》 (1989)
侯季然:请导演谈谈电影拍摄现场的情形,譬如你会营造什么样的气氛给剧组人员,让他们把你想要的东西做出来?
北野武:日本的片场制度是承袭黑泽明、小津安二郎那个时代的传统,就是导演至上,导演的指示就是一切,每个人都要听命行事,现场拍摄也是很紧绷的状态。但是我的北野组比较不一样,我的剧组会觉得不能放着导演不管,大家要同心协力帮助导演才行,有点像在长照北野武的感觉。感谢他们啦。(全场笑)

北野武与黑泽明
侯季然:导演的片子有非常多定镜、静止的镜头,会先跟摄影师沟通视觉设计跟镜头的使用方式吗?另外在拍摄之前,会先跟摄影师讨论分镜吗?还是到现场才分镜?
北野武:我认为摄影跟灯光是同组的,像夫妇一样的关系。通常我拍电影是摄影指导先走一遍他希望的镜位,然后侧拍给我看,说明等一下会怎样拍。我看了之后如果觉得可以,就会照摄影师的方案去做,如果我有其他想法的话也会提出,比如在哪里停下来之类的。但偶尔会遇到我的要求太多,以致于摄影师无所适从,那我就会说不如定镜别动了吧。也许摄影师对运镜有很多想法,想多动一下,可是被我限制住了。
侯季然:在导演的电影里面,暴力的展现是很著名的,但是这些动作并不会设计感很重,比较像是那种很日常的踹人,或是突然用头去撞对方,都是感觉很真实的打斗动作。像这些场面或动作,都是导演自己去设计出来的吗?
北野武:一般拍电影都会有动作指导,但是我作品里的拳脚动作都是我自己设计的,而且动作场面的摄影机会从一台变成三台。刚刚提到我的暴力场面很真实,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没有亲眼看过人被殴打或被杀害的现场。除非是经历过战争的人,不然一般人在现实生活中不会目击这样的场面,看电影也许会觉得很真实,但是实际上也不懂何谓真实。所以我能做的就是设计影像,让大家相信这些场面接近真实,但是会避开过度残忍的呈现方式。就像前面提到过的,我会把自己当成观众,去掌握「暴力」的底线。如果我自己看了觉得还可以,顶多视觉上有点痛而已,那就会放行。但如果超过容忍的范围,连自己都看不下去的话,我就会忍住,不会跨越尺度。

北野武《极恶非道 》 (2010)
侯季然:导演在拍片的时候会考虑预算吗?你跟出品方或监制方式维持什么样的关系?你觉得什么样的关系比较好?
北野武:我会把想拍的电影剧本给制片看,愿意拍的电影公司就会拿得出预算,案子是他们自己选的,所以很少遇到没有预算的状况。其实我手上还有更多想拍的剧本,但可能卡在预算的问题,没有公司愿意买单,因此没有机会拍出来。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没有什么在预算上吃过苦头,但也许在我身后有些人吃了很多苦头(全场笑)。

导演北野武在《极恶非道2》片场
剪接的因数分解声音与音乐对影像的辅助
侯季然:导演除了自己写剧本之外还自己剪接,能不能谈一下剪接的想法?怎么看待剪接工作在制作电影里所扮演的角色?
北野武:我在剪接容易去计较秒数,而且我偏好以奇数为单位去剪接,像1秒、3秒或5秒这样加下去,不太会用偶数。如果用数学的方式去思考,1+3=4,4是2的二次方;1+3+5=9,9又等于3的二次方,只要用奇数的秒数就能累积出某个完整的次方。
我也常运用「因数分解」的概念,譬如犯人A要去枪杀三个人,我们叫它X、Y、Z好了。如果用正常的想法就是AX + AY+AZ,要有A去枪杀每一个人的画面。但是我会先用一个A持枪的画面,然后再拍X、Y、Z三个人的尸体倒在地上的画面,这就用到了A(X+Y+Z)的数学公式。
还有一件我在剪接时比较注意的事,就是我会把没拍好的东西想办法剪掉。看起来拍很烂的画面,我会尽可能在剪接时让它消失。

北野武《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1991)
侯季然:导演的电影里常常不吝惜的有寂静跟留白,在声音设计的部分导演是怎么想的?
北野武: 我认为世界上既然有默片存在,代表对电影而言声音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声音要有辅助或帮影像加分的作用,不然我会尽量让声音不要打扰影像。不过我很讲究一些音效,比如东西落地的声音,或是枪声、刀声等,我希望那些声音趋近真实,所以会让音效师到美国,请他用拍摄时设定的枪枝型号做实弹射击,把最真实的声音录下来。刀的部分也是一样,尽量以真实的东西去收录。不过在声音这部分,原则上我还是会尽量减少,做到「声音是影像的辅助」的概念。
侯季然:请导演接下来谈一谈对音乐的想法。导演长期跟配乐家久石让合作,你跟配乐家是如何沟通的?是在拍摄之前就有音乐的demo,还是拍完之后再来想音乐?
北野武:刚刚提到的久石让,我跟他在《菊次郎的夏天》、《花火》都合作过。当时我单纯就是想要钢琴曲,所以很具体地跟他说,我喜欢乔治温斯顿(George Winston)的《Summer》,然后直接放给他听,要求他帮我写个类似的音乐,后来就有了《菊次郎的夏天》的配乐。这样说出来,好像对久石让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在邀约时有提出满具体的指示。至于其他黑帮暴力类作品的配乐,我会请配乐家创作最不适合那场戏的音乐,用音乐制造出冲突的美感。但是因为我要求拿出最不适合的音乐,所以经常都没用上,因为真的不适合。(全场笑)

久石让与北野武
侯季然:我想借此再追问一个问题,在导演的作品《盲剑侠》的结尾,有一个盛大的歌舞场面做为结束,配上非常欢快、节庆般的音乐,那时候是怎么思考这场戏的?音乐和歌舞场面是在剧本阶段就设定好了吗?
北野武:其实《座头市》的结尾我烦恼了很久,后来决定用村庄的祭典作为结束。但又不是有歌舞升平的场面就好,刚好我当时迷上了踢踏舞,自己也很常跳,所以我去找我的踢踏舞老师商量,有没有可能把踢踏舞的元素放进时代剧里?为此我们也去做了一些研究,当年村民会穿的草鞋、木屐有没有办法跳踢踏舞。后来老师认为可能没有办法发出很响亮的踢踏声,但是要跳出节奏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就让演员去练习,印象中他们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练习踢踏舞,结果那个结尾很欢乐,我自己很满意。

北野武在《座头市》 (2003) 片场
能够成为创作者真的是非常幸福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
侯季然:导演的作品写实呈现了日本社会的多元面貌,想请导演聊聊,你的电影作品跟现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会不会用电影去回应现实,或是现实发生的事件?
北野武:基本上我对日本的政治已经处于放弃的状态了。我身为一个国民,有尽到国民的纳税义务,也不做坏事,但是我不会透过自己的电影去批判政治,也没有强烈的意识要让社会更好,我只是想拍出让大家开心的娱乐作品,能够取悦众人就够了,而国家应该要成为在背后支持创作者的角色。
侯季然:导演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里,不断创作出很棒的作品,你是怎么保持对事情的敏感和创作的热情?
北野武:其实我现在已经在筹备下一部电影长片了,之所以可以这样持续创作下去,是因为我总是觉得下一部片才会是最好的。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作为导演常常被问:「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部作品?」,其实很多导演都想回答:「我最喜欢的作品是下一部」。还有一个也常被问:「你下一部片是怎样的作品?」应该很多人都会说:「如果能用讲的,我用嘴巴拍片就好了。」
侯季然:想请导演聊聊,从事电影艺术三十多年来,对电影有什么样的理解或体悟?
北野武:我跟电影相处的方式是这样子的,这次新片《首》已经是我第十九部电影,长年持续创作的动力,有一部分来自这些作品中有被大家认为是失败的,也有些被誉为杰作,评价好坏参半。如果每次都是好评,我可能拍个两、三部之后就收山了,相反的,如果负评如潮,我可能就没有信心继续拍下去。很幸运的是,拍到目前为止,刚好每部作品都能获得一些好评,让我有勇气继续创作;同时也少不了批判,让我觉得这次还不够成功,还有继续改进的空间。所以我认为我以后的作品,依然不见得会在世界各地广受好评。如果有零负评的那一天,那对我而言就是失败的作品。

北野武《首》 (2023)新闻发布会现场
侯季然:导演刚刚提到,有些作品被认为是杰作,也有些作品被认为是失败,那你是怎么面对过去被认为失败的作品?
北野武:常有人说我哪部片是失败作,对我来说,就很像父母看待不成材的孩子一样,我的作品就算有几部评价不高,看起来很糟糕,但是在我眼中都是自己的孩子,每个都很可爱。
侯季然:现在看电影的环境,因为科技的关系已经变得很不一样了,流媒体平台或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对于导演来说,你心目中电影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在现在这种新的观影环境里面,你觉得电影的珍贵之处在哪里?
北野武:我认为电影还是要在大银幕、声光效果好的剧院里面看,才是最好的体验。现在的观众可以选择非常多不同的媒介,透过手机、电视来欣赏电影,我们不太确定整个娱乐产业接下来会往什么方向走,但我个人会希望观众透过大银幕欣赏电影作品。同时我也蛮期待接下来的时代会带给我们的变化,不知道AI会不会创造出比现存的戏院更有临场感的体验空间?也听说过现在可以用人工智慧来写剧本了,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个人很期待电影产业接下来的走向。

照片来源:金马影展
侯季然:想请导演聊一下,以你多年拍电影的经验,你觉得当一个电影导演最重要的是什么?
北野武:通常电影导演都是很爱电影的,但是在我个人容易比较客观地去看待电影以及电影从业人员,我认为要当导演,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许我应该更爱电影一点,但我不想把爱电影挂在嘴巴上,而且我习惯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作品。
侯季然:最后我想要请导演,给新导演或电影人一些建议或提醒。
北野武:我无法给出多了不起的建议,我认为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缺乏食粮和饮水的地方,短短几秒内就会有很多人因为无法温饱而失去生命。人类要为了生存而进食,为了温饱而工作,然而日本和台湾很幸运,大部分的人都处于衣食无虞的状态。
我们之所以可以追求艺术,就是因为不必担心下一餐在哪里,这是个很宝贵的时代,当人类连温饱都有问题,就很难把注意力放到艺术上面。不必为了生活而工作,能够成为创作者,生活在追求艺术的状态中,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我希望大家踏入这个行业,要随时保持好奇心,对很多事物抱持兴趣,多吸收、多认识;然后永远当你自己作品最大的粉丝。只要你心里记得这份感恩的心,那一定没有问题的,大家加油。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CYQY-生活与科技 » 北野武:基本上我对日本的政治已经处于放弃的状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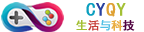 CYQY-生活与科技
CYQY-生活与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