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导演孙宁忆与中非导演帕斯卡尔·阿珀拉·吉内金迪联合执导的纪录片《吃苦》于今年年初在哥本哈根纪录片节首映后,已在全球多个电影节巡映,好评如潮。该片将于11月9日在纽约市纪录片节与更多的北美观众见面。

《吃苦》借用中国在中非设有多个基建工程队的背景,顺着建筑材料供应链探索,将镜头聚焦在产业链下游的采砂工人托马斯,与中国建设工程队的负责人栾建民身上。一个本国人在本国务最辛苦的工,而外国人在异乡的工作也复杂而繁重。影片探索了两个身份与背景迥异的个体的相似之处,也谈及了他们的家庭与个人生活。在中非持续的动荡与贫困中,吃苦耐劳者的生活侧写比“苦”字能呈现的更为丰富和精彩。

孙宁忆曾于塔夫茨大学攻读国际关系,毕业后曾为联合国效力。与电影学院毕业的电影人相比,她显得更加实际和接地气,作品力求呈现而不着重于表达。她本人有一种雷厉风行的气质,对于《吃苦》这部影片,她是身兼数职能者多劳的角色,对于记者,她是个非常好聊的对象,语速很快,表达自由,一个提问会让她开启话匣成为“自动档”。我惊叹于她丰富的经历与广阔的视野,也钦佩她敢想敢做、不会就学的勇气与决断。《吃苦》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电影人的长片首作,是一张像她本人一样优秀的答卷。(本采访含6388字。)

孙宁忆
——————采访正文——————
导筒:看了你先前的一些采访,你在班吉最开始是为了联合国工作,就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给联合国工作的背景?那个时候你在班吉的工作是什么内容?后来又是为什么改行做电影?
孙宁忆:我当时在联合国做志愿者。我研究生在塔夫茨念的国际关系,毕业之后来找我的工作都是想用我的中文能力,我想我花这么多钱学习也不是去干这些的,所以还是想用我学到的东西,或者发挥我的长处,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我当时就问了好大一圈人,跟人喝咖啡就喝了50个,打电话又打了50个,最后听说如果想进联合国系统的话,就得先去所谓的“field”,所以我就决定去做。我报志愿者被选到了MINUSCA(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维稳团,United Nations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ed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2019年9、10月那个时候去的。在中非有最主要的两个问题要注意,第一个是身体健康,因为你可能会得疟疾,要是不吃预防性药物就有可能会得,但是预防性药物对肝脏不好,长期吃下去不行。第二个挑战是mental isolation,班吉虽然是首都,但对我们来说可能就像最大的村一样,大家都认识,就这么几个酒吧、几个餐厅,时间长了,你的状态就会不太好。后来我确定了那里没有榴弹或者恐怖袭击之后,就决定去了。
一开始我的工作是Civil Affairs Officer,在首都挺幸运的,我要看我们12个驻地办公室每天发的报告,了解哪几个武装组织要打架,核实各种信息,再递交给军方看要不要行动。首都之外更艰苦,我有两次出了班吉,其中有一个地方常年都是40度以上,很干旱,也只能在联合国的营地里待着。班吉这个城市你好歹能自由出入,还有河。那两次出mission让我增加了很多对中非的一些底层民众的了解。
电影是2020年9月开始做的。我之前一直喜欢表演,从小就对演员很好奇,但是家里面没有干这个的,自己也不敢去想。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有上过表演班,跟朋友就是主持关于美剧和美国的一些播客,那时候有工作,还能在业余的时间去做这些自己很感兴趣的事情,就感觉很幸福。我就这么记住了:让我幸福的状态就是除了工作之外,我要做一些跟娱乐、电影有关的东西。去到中非之前,我在领英上搜到一个人,自己有纪录片制片公司,于是对方发了邮件约见面。他说中非这个国家报道很少也没人知道,要是想有兴趣的话,可以拍一个短片,他来做EP(监制)。我说好,他就教我看了三四部片子。到了2020年8、9月,我在班吉河边喝咖啡,看到本地人去河中间,回来的时候拉了一堆沙子,画面非常美。我问了之后知道这是一个下水挖沙子的工人,挖出来之后卖沙子给别人,其中有中国人。我想搞明白sand supply chain(沙子供应链)就可以拍个短片了。EP后来问我要不要找一个co-director,我就找到了中非的法语联盟,法语联盟确实培养了几批年轻的电影人,他们给我推荐了帕斯卡尔(《吃苦》另一位导演),就把她拉进来了。

那个EP后来因为一些原因退出了这个项目。我的制片人是马修,我们俩是战友般的情谊。项目开始我们就开始去参与创投了,他投了Hot Docs(多伦多纪录片节)和IDFA(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IDFA应该是第一个给我们钱的,Hot Docs中了我们就更加惊喜了。这时候就开始在中非拍。最大的鼓舞是圣丹斯,大家都很开心,我就意识到这个东西可能真的是大家想看的,那要好好拍。拍到一半我在纽约找到了工作,从2021年3月开始远程导演了一段时间,再后来我感觉中国人的故事还差一个高潮。因为班吉的拍摄团队是本地人不懂中文,收集的素材达不到最理想的状态,我就在2021年底到2022年的中国新年期间回到班吉去拍,当时回了北京学了两个星期的摄影,然后在班吉拍中国人的部分,嫂子(片中人物)的部分大多就是我拍的。拍完的时候我们有150个小时的素材,后期整个就是在纽约做的……对你看我都直接没停,全给你讲完了。

导筒:刚才的回答中你提到帕斯卡尔,你们是在那边就直接认识了。除了导演是被引荐的,剧组的整个班底是怎么建立的?
孙:说起来挺搞笑的,我找人推荐DP(摄影指导),先是推荐过来一个男孩,看着还挺好但有一次就没来工作。中非有宵禁,早上五点之后才能出门,我四点多就出来,但他没出现。那天我让录音师去拍,结果拍出来的巨好,比那男孩还好!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录音师是那个男孩的老师。我就说行了,正好那个男生喝酒又不来肯定要被开掉,就直接让录音师变成DP了,然后另找了一个录音师。总之我们一开始人就很少,一共就六个人……最开始那个EP,我,帕斯卡尔,制片人,DP,录音师。

导筒:六个人竟然拍摄了150个小时的素材……
孙:(笑)太疯狂了,当然了后来我在中国拍的时候,我还找了当地的女DP拍嫂子,八天拍了两回。
导筒:我查了一下班吉,它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这城市现状是怎么样的?
孙:它不是那种榴弹般的威胁,但确实有很多困难,比如水电不是长时间供的。外国人在这里会建一些住宅楼,只给旅居的外国人住的。所以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外国人住着有24小时水电的很贵的地方,本地人根本住不到。对中非人来讲,一开始被法国殖民,现在这么多外国人在中非看起来过得还挺好,可是为什么他们自己还是这么穷,这个疑问就会一直在心底。有的时候出了什么事,他们的怒火就会突然爆出来,这个是它危险的地方。我们在联合国最危险的是出车祸,平常没事情,但一旦比如说有个军人喝多了,开车撞树上,旁边的本地人就会突然开始向他丢石头,砸到他脑袋就会让他昏迷好几天。不安全的方面在于那种不可预测性,不知道为什么民众的情绪就会被煽起来。平常的话,班吉作为首都是由政府控制的,人口很多,资源也最好,所以是相对安全相对稳定的。危险的是出了班吉之后,你就不知道外面的区域是哪一个武装组织控制的,就会有切实的危险。

导筒:你描述的班吉的样子,和《吃苦》这个片子呈现的当地风貌,其实不怎么出乎我的意料。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在非洲有各种工程,人们其实会对电影呈现的内容和环境有一个预设的,也会想到动荡跟战乱,这些内容在你的纪录片里其实也都有。有没有一些你在剪辑的时候觉得会刷新大家对中非印象的内容?
孙:这个片子挺微妙的,它没有一个很强烈的观点。中国人的部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应该不会说太陌生。我倒是发现欧洲的观众觉得还挺新鲜的,因为想到中非就是战乱,但没想到战乱之中大家也要正常的生活,追求爱情和事业上的成功。他们也没有想到中国人跟中非人很多地方是相像的。这个是我挺满意的一个结果。我没有很深地去聊中国人这个整体对于非洲国家的影响,那是另外一个片子。我还是更想拍individual-driven story(以个体为驱动的故事)。
有个我很想拍但是没拍到的部分,你在片子里也看到,栾哥(栾建民)的工地出了事故,死了一个人。出事了之后立马现场就关了,我们也进不去,但你还是看到了一点点。栾哥这个人很坦荡,后来我们又和他聊这个事情,他就很直接地说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但是也不够,因为人家还有个三岁的小男孩,其实栾哥是真的很有同情心的。最精彩的是栾哥当时去了那个人的葬礼,非常勇敢,嫂子还跟着去,他们俩的感情是真的真挚。嫂子没敢告诉我,因为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外国人出车祸大家都那么容易激动,所以现场肯定很危险。回来嫂子忍不住跟我讲,他们俩去葬礼的时候,栾哥就是真诚的想表达愧意,他带了自己的一些本地的工人,那些工人就有点想保护他,受害者的家庭当然很生气,所以现场是一波中非人想保护他,另一波中非人想弄他。所以这肯定不能拍了,一定会出事的。但我觉得如果我拍到了,会影射了一个更大的主题,就是中非人民,或者说任何一个我们一带一路触及的国家,它对中国人的情感依附是基于经济需求,但另一方面是文化的差异,任何外来人造成了本地人的死伤,本地人肯定是很生气的。这个事如果拍到了,就会映射出一个更大画面的东西:本地人对于外来人口的一种复杂的情感。这就会把影片带到另一个层面。

导筒:你刚才说你还是更想拍individual-driven story,选的其实是两个主角,一个是栾建民,一个是托马斯。为什么会选这两个人交织在一起,把他们放到“吃苦”这么大的一个主题下?
孙:在沙子供应链上,托马斯在这个链条的最底端,栾哥也不是最顶端,但他至少是个买家。托马斯会下水,他干的活最苦,是最底层的,但他干活的画面还挺美的,所以想选他。我们也认识了一些别人,但是他们都不如托马斯爱唱歌爱表达,他故事性好。
栾哥这方面,要说中国人在非洲和当地人成为朋友,这个很少。之前有一个新加坡观众问我,中国人去非洲的移民跟新加坡移民有什么不同?我说新加坡移民会新加坡化,但中国人去非洲没有非洲化,大部分情况下他去非洲就是为了赚钱,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以后回国的时候更好,跟本地人有交流但仅限于工作。像栾哥这样,和本地人有来往,还给人家搞party、去人家葬礼的,是非常少见的。

导筒:托马斯最吸引我的一点,除了像你刚才说他挺有戏的,他给我一种很玩世不恭的感觉,他跟妻子相处不好,就回前女友身边,前女友有他孩子,他老婆也有他孩子,他的责任感和家庭观其实好像都没那么强。尤其跟栾建民对比,栾哥对嫂子那么好,责任感和家庭观都特别强,就衬托马斯特别风流又特别孩子气。但是他追求爱情,特别向往自由,这个态度又特别现代。我觉得可能托马斯的这个性格是整部片子里面最具有现代感的那一部分,你在哪里都见过这种人。人们对于非洲的那些印象和想象,其实在片子里面的呈现并没有实现什么超越,但可能到了托马斯就有了一种超越。
孙: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挺有意思的。所谓的农业社会,它的性别分工很强,女的照顾孩子,男的要赚钱,这个事如果有一方办不好就会出问题。托马斯属于那种……他找的女朋友其实都挺像他妈妈的,都是特别有自己想法的女性。我后来问我的团队他们对托马斯的想法,用当地的说法,就觉得托马斯一个“没有project的人”,因为中非年轻人特别喜欢说“我有一个project。”他们就觉得托马斯太随意了,没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心里没谱,但是这种性格很适合做艺术家。一开始托马斯说自己是音乐家,所以我的团队就去多听了听,发现他还录歌,就觉得很有戏,大家都是后来才知道他女朋友这么多。其实他要是生活在一个很好的家庭,搞不好这些灵感都可以写在歌里。
导筒:在这部片子里,我觉得虽然托马斯和栾哥两个男人看起来是冲在最前头的、最吃苦耐劳的人,但他们周围的女性其实也都在跟着他们吃苦的,只不过吃的苦是不一样的。你是怎么收集她们的素材,在剪辑上怎么做出取舍的呢?
孙:拍电影有一个额外的因素,就是运气,我们的运气就是所有的女性角色。我们都不知道托马斯的妈妈这么牛,她直接对托马斯说:“她走了,你再找新的,新人还会走。”嫂子就是一点都不装,有啥说啥,偶尔也爆粗口。女性角色会出现是因为她们是他们(托马斯和栾建民)的家人,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么精彩,她们柔化了这两个角色,让两个男人突然有脆弱性了,再加上嫂子和栾哥又特别爱开玩笑,所以又增加了幽默。这些东西一出来,你肯定想把它加到片子里。当时栾哥只是跟我说他老婆要来,我说你让我拍,他说行。嫂子又信任他,所以嫂子也同意了,我就拉了DP去山东拍。托马斯是同样的,他妈妈就不介意,拍了托马斯就可以拍他的家人,他女朋友什么的顺带就都拍了。

到剪辑的时候,我们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剪辑,因为这两个人(托马斯和栾建民)不是朋友。所以我们按照主题来剪,比如先是家庭,再是生活进展,一个接一个。前半段还是关注在职业和家庭背景,到后面就完全进入到他们的家庭生活了,所以女性角色就越来越多。
导筒:你怎么找到栾哥的?
孙:一开始我找了两个月,在那边聊了很多中国人,都差点劲。其实中国人在海外的生活挺无聊的,白天工作,晚上看电视,晚上也没什么娱乐。当时我一直说找不到合适的,就找了栾哥的老板何姐。何姐是在那边驻扎下来了,在那边有一个30年的中餐厅。何姐说你跟我的员工小栾聊一聊。我说行吗?她说对,山东人,聊一聊。
我跟栾哥聊了两句,我就知道是他。真的是首先他很淡定,然后他知道自己是谁。你问他:累不累。他就直接说:太他妈的累了。这个人很真实,他没有想表现的想法,一点都不去粉饰。我们说拍一场,他也不管摄像机,他很忙,而且他是让你不要占他的道,你只要不挡他的道你就随便拍,这简直太完美。他也有不高兴,不高兴也表达。第一次拍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纽约连线采访他,网络不好,再加上信任我了,他就说家都四分五裂了,不高兴。他没有要掩饰什么的。我觉得栾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他愿意去表达出来,所以找他找挺准的。

导筒:拍摄期间除了班吉本身自带的恶劣条件,加上疫情,中非的防疫情况是怎样的?你们中间有没有断过拍摄?有人生病过吗?
孙:一开始我们联合国的都有点紧张,怕第一例是出自于联合国,这个就很容易引起民愤。因为发热嗓子疼跟疟疾有点像,所以很多中非人就觉得是得疟疾了。其实平常他们就会因为各种毛病生病或者是死亡,没有人真的去统计到底怎么死的,除非后面真的出现了大量的突然的死亡,但一直没有出现。在中非,一个房子和另外一个房子之间能差出来50米,很通透,又一直开着窗户,就一直没有发生我们想的情况。等到真的疫情全球开始了之后,让大家戴口罩,他们也不会特别认真戴。一开始联合国人很重视,所有外国人都戴着口罩,后来大家发现好像真的没有死伤的情况,又被中非人不是很在乎的状态所影响,班吉就没人戴口罩了。那个时候真的太奇怪了,很魔幻,所以我们的拍摄没有受任何的影响。到最后整个非洲好像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
导筒:疫情对片子的拍摄没太大影响的话,其他的难处也是很多的吧?最难的是什么?
孙:我做片子一开始没有想结果,只是一定要先把它做出来,而且我是co-director,我还有另外一个导演,大家要都要互相尊重。最难的还是团队合作,一说起国际合作、国际团队,听着很棒,但现在我听到就头疼,真的是太苦了,文化差异太大。这不是说一种表层的不同,比如你跟美国人有文化差异,但是大家生活的节奏和工作的观念都是类似的。中非人很慢,一开始拍摄他们迟到,我就哭,我说不知道怎么合作,他们没有这种干什么都要跟对方打电话的习惯,后来他们就为了我开始打电话。他们的生活可能随时出事儿,比如暴乱以来就会有变化,所以也不会有一个时间表。他们如果跟你约好了一个时间,你没来,他就走了但也不会生气。

我有一次和帕斯卡尔说,你要多干一点。她说你自己做饭吗?我说很少。她说你自己洗衣服吗?我说不洗。她说你缝衣服吗?我说不缝。她说这些东西我要自己做,我还要照顾弟弟妹妹给他们缝衣服,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睁开眼睛就可以工作。你就意识到,睁开眼睛可以工作,竟然都是一个特权。她说完这个之后我就闭嘴了。后期我和马修把所有都干了,包括公关和社交媒体的宣传。我的制片人他干的是我们所有人中最多的,他心中一定是很苦涩的,但是也没有人问他辛苦不辛苦,因为他是个白男,还是前殖民地国家来的。我们150个小时的素材,有70小时是桑戈语和法语的,最后翻译成英文,这都是制片人干的,我们俩从后期开始的工资都没有发过,但当地的工作人员的钱都发了。
对于帕斯卡尔来说,肯定也有不爽,比如为什么后期不放在法国,你放在纽约我很不方便,你为什么不把所有的素材都翻译成法语字幕让我也看懂。她有这种要求很合理,我当时说这等不了,我们没有钱,现在的钱全都是给剪辑师的,反正你都知道我拍了什么,我都跟你说过,而且你也去过现场,所以你就不要追求说你还能有所有的字幕了。所以她肯定也有不太满意的地方,这种合作还是有一点别扭的,真的是磨合。做纪录片太苦了,帮你的人太少,然后你就总是拿不到钱自己在那生干。

导筒:整个项目从开始有概念到完成花了多久呢?
孙:组团队这些差不多是两个月,差不多从2020年的8月到10月,然后10月开始拍摄,15个月的时间,一直拍到了2022年2月过年拍完。后期是8个月,其中剪辑五个月,我们真的是神速,那会我跟马修已经心理状况都不太好了,两个人压力大的有点睡不着觉。我们两年做出一个纪录片,这不是疯了吗?我那会有时候开玩笑,做这个片子就跟爬喜马拉雅一样,反正就是爬一次很有意义,再让我爬我可不爬了。

导筒:你下一部作品是剧情片,是以一个在法拉盛的一个亚洲女性为主角的,可以讲一下吗?
孙:在纽约的时候我报了一些演员招募,碰到了一个男生,跟我说他一直在等一个中国人跟他合写宋扬的故事。这个事《纽约时报》也写过,是2017年11月25日在警察对宋扬的一个突袭当中,她情急之下从楼上坠下来了,至于是有人推的还是自己跳的,没有很明确的说法。我后来做了大量的调研,查性工作者在纽约的生存状态,也联系到了宋扬的家人,就这样开始了。我很喜欢宋扬的故事,我在她身上看到我自己,她想到就一定要做,但在这个过程中她进入了性行业。现在有时候在工作中我不开心,不就是为了钱在付出自己的脑力跟体力吗?所以我不一定去做性工作,但是我认为情感逻辑是一样的,你的选择不够,你就只能做现在你能做的事情,你要再有野心那就更麻烦了,会更容易被卷入撕扯当中。我看她的故事,会觉得这个人一直在主动去争取些什么,只不过她失败了。
我很感谢那个男生找我去开始做,最后他退出了,所以我现在自己在做。又因为《吃苦》认识到了其他很多优秀的女性,然后就有两个女制片人听说我要再做宋扬,就说那我们愿意帮你,让我写好新的内容给她们看。这个跟纪录片太不一样了,我觉得还是这个项目对你招手,你就去干了。


导筒:你会想演宋扬吗?
孙:我一开始想演啊!所以想找别的女导演来导。有人推荐了几个文艺片导演,我看了那些片子,觉得太氛围性了,宋扬的故事实实在在的移民经历,即便是形而上的表达也要基于真实,不是靠这种氛围。所以我就意识到,还是应该我来拍,那我现在要去学,一次就要拍一个好的。我曾经问我,你有多在乎这个东西?我说在乎到拍完了我可以去死。(笑)所以我一定要把我能给的都给她,但是不能我想干啥就干啥,所以演不演到时候再说吧。
采访 / 撰文:蓝詹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CYQY-生活与科技 » 跟随这部中非合拍纪录片,深度直击打工人之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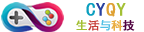 CYQY-生活与科技
CYQY-生活与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