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柳青
看《有生之年》的前四集,感受大致相当于走在台北街头喝珍珠奶茶,茶不名贵,但是轻易可得的小确幸。
《有生之年》也像珍珠奶茶一样,是台湾的环境里生出的「特产」。
不奇怪许多内地观众纠结于它的「生活流」有「悬浮感」:为什么快30岁的小伙子能安于在家庭作坊的早餐店里帮工?为什么中年主妇在赛百味打零工都能显得体面?为什么老母亲把大半生积攒的100万(台币)投给儿子的餐馆、血本无归后她还能保持情绪稳定?为什么所有人没有高学历、高薪酬,在黯淡的生活中却一点不焦虑?

《有生之年》
这些质疑没有问题,剧也没有问题,只不过因为这样的作品是在别处的土壤里长出来的。
《有生之年》上线的第一周,它在内地社交网络上的热度远远不如《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特稿,那篇文章白描了一个在过去五年里被困在考研考编死循环里的大学毕业生,她和她所在的世界被学历、体制、世俗认可绑架着。
在「上岸」成为信仰且弥漫着歇斯底里焦虑的环境里,远远观望《有生之年》,那里的一地鸡毛都能被当作普通人的乌托邦。

三联特稿
「有生之年,能长这么大,算不错了。」故事开始于41岁的高嘉岳决定去死,他在屏东琉球乡经营的小饭馆倒闭了,处了多年的女友怀了别人的孩子。
人到中年,高嘉岳做什么都半途而废,不了了之,连求死也是。
一个世俗意义的loser浪荡儿,赖活不行,好死也不行,他成了一个卡在缝里的尴尬人。
万念俱灰中,他烂醉返乡,给自己制造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结果一头撞进家人们鸡飞狗跳的生活。他在异乡过得不好,回家一看,故乡的亲友们也过得乱七八糟。
父亲知道大儿子醉酒的劣迹,担心他沉睡中呕吐窒息,整夜不睡地守着。这个看起来含辛茹苦的老父亲又是个极为自我中心的糟老头,面对同一屋檐下的妻儿没有同理心,每天惦记喂鸟喂狗也不会给妻子提供任何情绪价值,对小儿子呼来喝去,对比以上种种,他肖想年轻貌美保健护士的那点色心都不值一提。

母亲操劳大半生,和丈夫共同经营早餐店几十年,拉扯三个小孩成人,但夫妻之间两两相望只剩失望。
母亲被这个家捆绑太久,无论经济还是心理都已无法断舍离,她只能在逼仄的老宅里和丈夫分房,没有一间可以出走的自己的房子。她当然是不甘心的,于是只能做个暴躁怨妇,走投无路的她让身边至亲也走投无路。
老二为了维持和睦大家庭的气氛,大事小事忙得团团转,他看起来是完美儿子、完美兄弟、完美丈夫、完美父亲,但很多时候,他的尽善尽美的「努力」触犯所有人的真实意愿。
老三是典型「全职儿子」,和父母同吃同住,帮忙打理早餐店,像未成年的孩子。然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三人,是互不了解的熟悉陌生人。

在乏善可陈的庶民生活里,人人焊着面具把守「隐秘的角落」,带着最大的秘密返乡的高嘉岳,好像皇帝新装里捅破窗户纸的小孩,他总是在不合适的时机短兵相接不合时宜的真相。
夫妻不响,兄弟不响,只有高嘉岳是不合时宜的人,不成熟的人,总是破坏气氛的人。
老高家的家庭氛围和相处之道,可说是「东亚的,太东亚的」。在这一点上,《有生之年》的剧作没能提供新的视角,也没有写出新的人或人的新意,它是在套路里的。

至少从前四集看,太多情节的走向可以预料,编剧的行动很容易被预判。诸如侄子网恋奔现时,找大伯顶缸,结果对方姑娘对大伯一见钟情;侄子帮爷爷找东西时,「恰好」看到大伯放在书桌上的遗书,他为了「拯救」大伯,一厢情愿地撮合他的网恋对象和大伯;生无可恋的大伯唯一放不下的初恋对象,又成了老三的女友……一次又一次,巧合推着情节走,巧合代替了戏剧张力,编剧搭建情节框架时,依赖着老梗和桥段,换句话说,在构建「戏剧真实」时,这个剧作是乏力的。
这个剧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从严重套路化的情节里开辟了生动的情境,编剧套用着八点档情节剧的模板,却捕捉到生活中细微的呼吸。
离家出走的老父亲趁妈妈出门旅游时回家,到家后他理直气壮地质问小儿子:「谁给我做饭?」大儿子看到妈妈拆网购的包裹,第一反应是抱怨「女人网购太多浪费钱。」
旅行中的妈妈想和小儿子分享难得的开心时刻,但儿子接通电话的第一反应是汇报老爹的现状。
正是在这些看似「闲笔」的细致末梢,编剧写出了东亚家庭内部让人膈应的权力关系和秩序。

当然最耐看的,还是把文本细节具象地带到镜头前的演员们。
如果把剧作类比一部剧的「骨相」,考虑到这剧只出了四集,不能太早断言它骨相不行。
而它的「皮相」是已经确定的,整个演员班底,尤其杨贵媚和吴慷仁,只要他们出现在画面中,就给这部剧制造出丰满耐看的皮相。
一旦抽离演员的因素,《有生之年》的这群主角是集合了当代生活各种符号的类型人物——老大擅长提供暂时的情绪价值,又极不靠谱,他的洒脱懒散总要人善后;老二是面面俱到的体面人,但很多时候他累,身边人也累;老三没什么志向,基本是妈宝;老爹是家庭土皇帝;妈妈过得辛苦委屈,又不能痛下决心放飞自我。
这样的「类型人物」拥有的特质让观众或多或少觉得似曾相识,可也是缺乏个性的。

所以这个剧最大的看头是找到了一群恰如其分的演员,演员以自己的个性完善了这些人物,在表演中给了角色辨识度。这部剧中「生活流」和「悬浮感」同时在场,「悬浮感」来自高度套路化的情节设计,而表演缔造了「生活流」。
吴慷仁的出场当然是吸引人的,烂醉的高嘉岳夸张地拥抱久别的家人,夸张地发酒疯,他放诞地表演快乐,以此遮蔽他孤立无援的悲伤,在谁都有秘密的这个家里,他其实是把秘密藏得最深的人。
吴慷仁善感且敏锐地把握着「大于生活」的表演尺度,因为高嘉岳是兴高采烈的悲伤小丑,他漫不经心又理直气壮地演绎着「表演出来的生活」。
作为对照,郑元畅谨慎且准确地维持着一种和生活尺度相符的表演,他轻描淡写地应对了各种抓马情境,他的尚未褪尽的偶像气息/包袱甚至成了神来之笔,二哥何尝不是生活秀里谨言慎行的「偶像」。

最丰富的还是杨贵媚,她出现在画面上的时时刻刻,定义着生活,进而质问了生活。「假靳东」和「秀才事件」让缺爱的老年女性成了话题,而话题意味着无数个陷在痛苦中的个体被抽象化了。
《有生之年》的杨贵媚还原了「社会话题」所不能概括的一个具体的女人,她在几十年家庭生活中被困于情感枯井的具体的痛苦。杨贵媚的泼辣、怨怼、爆发,她的含辛茹苦和荒唐滑稽,既创造了这一个高妈妈,又是无穷无尽影影绰绰的东亚妈妈。
尽管这个故事开始于高嘉岳,不出意外他也应该是全剧的C位,但很多时候,我希望镜头不要离开杨贵媚,想看着她走得比短途旅行更远,从高妈妈的身份里走出来,变成陈大姐,变成不是任何人妻子也不是任何人母亲的她自己,那将也是「有生之年」。说真的,谁知道高嘉岳返乡的后续会不会沦为男性中心的「乡愿」呢?

《有生之年》的第一个画面来自水下的视角,琉球乡的近海净澈如琉璃,庞大的海龟悠然游弋其中。后来高嘉岳和侄子谈心时说出,这是他险些自杀成功时看到的画面。

这是个浪漫的,也许过分浪漫的段落,它让《有生之年》看起来像一种改良后的新型「偶像剧」,不再造一眼假的空中楼阁,而是把生活黯然的那一面浪漫化。与其说这是台剧传统的「生活流」,倒不如看作「偶像剧」拓开了边界,吸纳了失败者的故事,用「戏剧真实」给「现实真实」裹上糖衣。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993113-生活与科技 » 8.7分算神剧吗?道尽了东亚家庭的权力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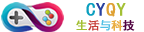 993113-生活与科技
993113-生活与科技










